侯马盟书研究新进展:叶培贵教授的独特见解


编号16:21 长8.4cm 透闪岩

本文选自《中国书法》2021年2期
“侯马盟书书法专题”P138-147

侯马盟书三题
叶培贵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摘 要:古文字的发展线索,应该有“明”“暗”双线。暗线就是手写字迹,但并未能够系统重建。侯马盟书及其前后时期的同类作品,在笔形和横竖画的走向上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特点,实际是属于楷行系统而非篆隶系统的,其产生的基础是毛笔的物理特点和右手执笔书写的生理特点。认识到这种特性,不仅对于构建文字史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有助于理解书法史上笔法和结构生成的基础。但正体的强大影响力,又会使文字在演进时并不单纯依赖毛笔的物理特点和右手的生理特点;与此同时,艺术化也会促使人们发现毛笔运动的其他可能性,使早期字迹在重新进入艺术场域时,也会被全新的笔墨所改变。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使历史资源获得更加富有活力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文字演进 “暗线” 笔形字形 生成基础 正体 艺术化
侯马盟书是中国文字史上的重要材料,也是书法史上不可忽视的作品,在文字史和书法史两个范畴内都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对侯马盟书进行讨论,这两个角度,缺一不可。笔者在进行书法史教学和研究中,获得一些浅陋的思考,芹献于此,求教方家。
文字演进的“暗线”
关于早期汉字演变的探讨,目前材料尚有许多欠缺。根据已知材料构建的演进线索通常是“甲骨文—金文—小篆与隶变”,由“隶变”而生成今体文字。然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以刻为主的甲骨时代、以铸为主的金文时代,书写也是比较普遍的存在,只是“典”“册”保存不易,未能充分参与到后世关于文字史的重构研究之中。
侯马盟书作为隶变时期的重要书写之迹,在文字史上因此占据了重要位置。
有理由推断,如果各种文字材料得到充分保留的话,古文字的发展线索,应该是两条:第一条是“明线”—以铸、刻资料为据,第二条是“暗线”—以书写字迹为据。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文字发展有“正体”和“草体”两条线。从材料角度看,高度概括地说,在古文字阶段,正体主要存在于“明线”也就是铸刻资料中,而“草体”主要存在于“暗线”也就是书写资料中。双线交互,产生不同样貌,影响文字体式和演进。李学勤、彭裕商认为,甲骨文中存在一种“简册风格”,窃以为就是保留了较多书写特点的刻契作品。铸刻不断地削弱书写中笔毫的表现,将古文字导向丛文俊教授所说的“图案化”方向,其结果是小篆的生成。丛文俊教授的“书写性简化”,应该分解为“铸刻性简化”和“(狭义的)书写性简化”。“铸刻性简化”将文字引向“图案化”,其构成元素趋向于文字学家所说的“线条化”。而“(狭义的)书写性简化”则将文字引向隶变,其构成元素趋向于文字学家所说的“笔画化”。启功先生说“字是写出来的”,又说“透过刀锋看笔锋”,虽然前者是宏观说法,后者指向的是碑刻文字。但如果循此以入,实际上已指出了这个重大理论问题。

编号16:2(正反) 长5.1cm 透闪岩
由“字是写出来的”追问下去,会发现,侯马盟书这类书写资料,牵涉文字史的,实际上远远不止于“隶变”也就是古今文字演变问题,还将牵涉今体文字的演进问题。
隶书为什么短短一个朝代就退出了应用?楷书取代隶书后为什么不再产生新的正体?
笔者在《行书教程》中,曾引用殷商时代的“祀”字陶文,指出其中的笔画形态特别是横竖起笔的斜切角、横画的向右上倾斜、竖画的尾部向左偏出等特点,其实源于右手的生理特点和毛笔笔锥的物理特点。而这三个特点,究其根本,与铸刻时代的正体的总面貌和发展趋势是相违背的。结合隶变普遍发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朱墨书资料,特别是侯马盟书等资料,同时参考汉代简牍隶书,不难发现,即便是在石刻隶书最为发达的汉代,这三个特点仍然广泛存在于书写资料中。
熟悉文字(书法)基本构成原理,则不难了解,这三个特点,属于楷行而不属于篆隶。经由隶变而形成的隶书,在文字“构形”上改变了篆体,但成熟的隶书在“造型”上却又回归到了篆体的横平竖直、左右对称、平行等分等原则中,广泛存在于简牍(手写字迹)中的上述三个特点也被舍弃。由此出现了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在文字学中“隶楷”文字并称,而在书法学中则通常是“篆隶”并称。其根本原因就是成熟隶书的造型原则和除了波磔之外的其他点画形式都向篆书回归了。
从文字的角度说,成熟隶书造型上向篆体回归,一方面方便了其正体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却也使其成熟形态又走到了“趋急速也”的反面,不采用藏头护尾等技巧而采用右手执毛笔自然书写的方法,是不容易获得成熟隶书的效果的。这一点,任何一位以东汉桓灵时期的经典汉碑为法的学书者都十分熟悉。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成熟隶书很快就失去了社会基础,而被更加便于书写的楷书、行书所取代。
楷书、行书的基本点画,完全满足了右手执笔自然书写的物理(毛笔锥体)和生理(右手执笔)特点,在右手执毛笔这一书写习惯和工具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文字形式已无进一步改造以“趋急速也”的必要性了。楷书、行书出现之后的文字改造,主要是减省笔画等,其最终结果是简化字。简化字并不改变其仍然属于楷书、行书的这一性质。

编号1:24(正) 长17.2cm 蛇纹岩 板岩

编号1:24(反) 长17.2cm 蛇纹岩 板岩
以上推论的最终结果是:窃以为,构成楷书、行书(今草)的基本点画形态(横竖起笔有斜切角、竖画尾部向左偏出)和结构形态(横向右上倾斜,导致无法实现左右对称)这些特点,并不是隶变(当然也不是汉代后期楷书、行书字体逐步成型)时期的产物,而是一直存在于手写字迹中的。它们始终作为一种“草写法”在冲击着正体字,并最终凝结为楷书、行书。这一条文字演进的“暗线”,仅仅依照“构形”的分析,是难以揭示的,只有从“造型”的层面上、从“(狭义)书写”的角度加以分析,才有可能得到揭示。
侯马盟书及那一时期的各种字迹,为这条暗线的揭示,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证据。遗憾的是,证据链仍然不够充分—前此的“典”“册”,还有待于进一步发现。
笔形和字形的生成基础
由以上讨论,可以进一步延伸的是笔形和字形的生成基础问题。
宏观上说,汉字字形和笔形来源于人对自然万物包括自身的观察,也就是《说文解字》所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但是微观上说,物象无法自行转化为文字,成字有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条件与手段。甲骨文笔形普遍呈现为两头尖、中间粗,主要是因为“刻”;金文笔形逐渐形成两头圆、整体粗细均匀,主要是因为“铸”。如果观察足够仔细的话,都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甲骨文还是金文中,都有一些作品保留着毛笔书写的痕迹,比如甲骨文的双刀刻辞、早期金文的一些作品,起笔斜切角笔形随处可见。
从理论上说,起笔形态可以分成“(狭义的)尖”“圆”“方”三大类(为便于分析,仅以横起笔形态为例,其他笔画的起笔形态以及收笔形态可以类推)。“(狭义的)尖”指的是起笔部分只有上下两个侧面轮廓,“尖”在起笔处,其典型形态就是甲骨文的单刀刻辞的笔形。“圆”可以理解为起笔处有三个侧面,但是左侧面为弧形,左侧面与上下两个侧面交汇处也是弧形,其典型形态是金文成熟时期以及经典小篆的笔形。“方”在起笔处,可以有“正方”“斜方”两类,“正方”在古文字阶段十分少见,其典型形态是汉代隶书石刻中如《张迁碑》《鲜于璜碑》等的笔形。所谓“斜方”,又可以包含两小类。第一小类是横起笔处的左侧轮廓向左倾斜,其典型形态是楷书、行书的横起笔。第二小类是横起笔的左侧轮廓向右倾斜,其典型形态是隶书的某些蚕头以及楷书行书中因为上一笔的映带而形成的横起笔(如《兰亭序》中“集”的长横起笔)。
以上诸种类型中,“(狭义的)尖”“圆”以及“正方”需要“刻”“铸”才便于获得,而“正方”的第二小类,则需要在起笔之际有特殊的回锋或映带动作才能获得。只有“斜方”的第一小类,才能由右手执毛笔,不需额外的动作,自然挥运即可形成。

编号1:43 长17.7cm 蛇纹岩 板岩
邱振中指出毛笔运动有“平动”“提按”和“绞转”三种基本方式,但是没有进一步充分讨论“右手”操控和“笔锥”运动的复杂性,未能就笔形特别是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笔形变化的基础和演进规律给出更加细腻的解释和描述。王凤阳《汉字学》谈到手写对点画系统的影响,“要写得快,就要顺应生理习惯”,提出“反逆性原则”,但遗憾的是,他仅仅讨论到了手的生理特点,而没有讨论到毛笔笔锥的物理特点,因而即便是在讨论隶、楷的区别时,也未能充分关注起笔处的形态差异,而把重点放在了收笔处是回锋、藏锋还是出锋上,错失了从造型层面真正区分成熟隶书与楷书之间的根本差异的机会。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和王凤阳都讲到“线条化”“笔画化”,并且认为隶书已经实现了笔画化。我们认为这个判断在“构形”层面上符合学理,因为隶书点画的生成基础已经不再是物象,但这个说法在“造型”层面上却也是不能完全成立的。如前所述,早期隶书确实实现了笔画化,但东汉后期以庙堂之碑和部分墓碑为代表的典型汉碑,则除了波磔实现了笔画化之外,其他笔画一定程度上是重新回归到篆体的线条了。
字形的情况与此相似。
决定字形的根本因素是横轴与纵轴。横轴由横画的方向决定,纵轴由竖画的方向决定。从理论上说,它们有四种组合方式:第一种是横平竖直,第二种是横平竖不直,第三种是横不平竖直,第四种是横不平竖不直。第二种又可以分解为两个小类:第一小类横平竖向左倾斜,第二小类横平竖向右倾斜。第三种也可以分解成两个小类:第一小类横向右上倾斜,竖直;第二小类横向右下倾斜,竖直。第四种则可以分解为四个小类:第一小类,横向右上倾斜,而竖向左倾斜;第二小类,横向右上倾斜,而竖向右倾斜;第三小类,横向右下倾斜,而竖向左倾斜;第四小类,横向右下倾斜,而竖向右倾斜。
纵观汉字史,第一种“横平竖直”和第四种第二小类“横向右上倾斜,而竖向右倾斜”占了上风。
“横平竖直”是篆书和成熟隶书的典型字形特征。
目前所见篆体的成字条件,主要是龟甲兽骨和青铜。龟甲兽骨通常纵向排列文字,若要寻求字形组织的参照系,最为便利的是龟甲的中间线。事实上,大多数完整的甲骨片上的文字排列,就是以龟甲中线为界,居右的行是从左向右排列的,居左的行则相反,以龟甲中线为整体排列的参照系的特点十分鲜明。中线的垂直特点,衍生为纵向有行、横向无列的行内处理方式,进而为保证行内的贯通。一方面限制字形的左右伸展(不少物象因此而改变了方向,如本来应该四脚着地的虎、犬、豕等字,变成了尾部着地、四脚腾空);另一方面力求单字横平,与竖直相互配合,构成单字的核心骨架,其他形式处理方法如平行、对称、等分等,在这一骨架上相应生成。青铜器物可以为铭文规划一片相对规则的空间(如正方形、长方形等),使得金文不仅可以在纵向上成行,在横向上也可以成列。换句话说,可以为每个单字规划出相对独立而且彼此大小接近的空间,由此形成字形的两种理路。第一种是进一步强化横平竖直的处理模式,最终演进为小篆。第二种是弱化横竖这类直线,而强化曲线对字内部空间的平均分割,但基本骨架仍然呈现为横向平、纵向直。“刻”尤其是“铸”的过程中的“制作性”(而非一次性完成的“书写性”)对字形构造原则的贯彻落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横向右上倾斜,而竖向右倾斜”则是楷书、行书的典型字形特征。

编号1:51 长14.8cm 蛇纹岩 板岩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后者的“竖向右倾斜”有时候并非整个笔形向右倾斜,而隐蔽地体现在竖画的末端:当末端为悬针时,针尖向左偏;当末端为垂露时,露珠在左侧。两个形态,都提示笔锋最终结束于笔画的左侧,换句话说,若由针尖或露珠中部向上画一条垂线的话,其位置实际上是偏于整个竖画的左侧的。若连线的上端所取的是起笔的中部,则连线是向右倾斜的。启功先生讲到楷书结构的“横不平”时,特别举了宋体字横画的右侧有一个小三角为例,可见“不平”主要呈现为向右上倾斜。如果借用他的方法,也看看宋体字的竖画,会发现在顶部右侧有一个小三角,而且尾部明显左轮廓短于右轮廓,提示了竖画的顶部向右、底部向左的特点。
无论是横画向右上倾斜还是竖画向右倾斜,其生成基础都是“右手执毛笔”的生理特点和物理特点。不管用腕还是用肘,控制毛笔运动的中心点,都在笔毫的右下方,横向书写时,向右上行进最为方便,纵向书写时,末端向左出锋最为方便。
“横画向右上倾斜而竖画向右倾斜”,决定了字形结构无法使用对称等平衡手段,甚至平行、等分等方法也需要有根本性的改变。经典楷书结构原则中有“上紧下松”“左紧右松”等口诀,就是这种改变的具体体现。例如,数横并列时,常常左侧间距近、右侧间距远,呈现为从左向右发散的样式。
“右手执笔”决定了楷书、行书字形的基本架构,是楷书、行书字体的字形构造原则的生成基础。《侯马盟书》以及其他手写字迹,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可以提供坚实的证据。
“正体”对“手写”的影响以及“艺术化”问题
以上两题,试图从手写字迹的若干痕迹,推断文字“造型”的生成基础。但全面考察手写字迹时,也会发现,其中的若干推论,在字迹上的呈现,并不完全充分,甚至在有些时候是完全相反的。
导致这种并不符合甚至相反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正体”的强大影响力,第二是“艺术化”的强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前者包含于后者之中。
首先看“正体”的强大影响力。
以早期手写字迹中的横画形态为例。许多字迹呈现了横的起笔处有斜切角,但整个横画却并不完全向右上倾斜,而是前半部分向右上、后半部分下压;有些居于字形上半部的横,甚至是整体下压的。因此,侯马盟书中的绝大多数字形,总体看来,仍然保持了篆体“横平竖直”的字形特点。
这种现象,在隶书发展成型之后的两汉,也是普遍存在的。
换句话说,在手写字迹的笔形和字形中,固然可以发现大量“非篆(隶)体”的形式元素,但并未因此而造成另一种字体(楷书、行书)。
这种现象毫不奇怪。在知识主要掌握于贵族手中、未曾全面下沉至平民的先秦乃至秦汉时代,承载国家权力意志的“正体”拥有最大权威,手写字迹不可能完全超越正体文字的规范。相反,手写字迹总要在字形、笔形的总风貌上坚持正体文字的基本体系。“非正体”的形式元素,只有经过不断的量的积累,足以凝定为一套新的体系之后,才能演生为新的“正体”。从文字史上说,手写对字体的体系性改变发生过两次:第一次产生隶书(以及章草),第二次产生楷书、行书(以及今草)。第一次改变了文字的“构形”,“造型”上却回归了篆体原则;第二次才在“造型”上彻底实现了以手写为生成基础。“隶书”一定意义上成为字体演进中的一个“曲折”、一次“(造型上的)返祖”。在此过程中,“正体”显示了强大的制约力量。

编号1:67(正) 长10.8cm 蛇纹岩 板岩
再看“艺术化”的强大作用。
“艺术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艺术化,包括文字的正体化追求,也就是文字学家所说的“规范工整有序”,甚至包括“非书法”的装饰性追求在内,郭沫若曾经把春秋战国时期的鸟虫书认定为中国文字艺术化的开端。“正体”的制约力已如上述,“(鸟虫书等)装饰体”由于承载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更是毋庸赘言了。
狭义“艺术化”的追求,按照传统书论,即是“翰墨之道”。目前通行的解释,它开始于汉末魏晋南北朝,那已经是楷书、行书、今草成熟的时期了。此后直至清朝前中期,“翰墨之道”主要就在楷行和今草三体内展开,演绎出极为繁复的笔法体系和结构类型。笔法体系不必赘言。结构类型中,沙孟海指出的“平画宽结”却值得加以讨论。“平画宽结”在隶楷错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源于“(篆)隶体”的结构影响,但唐宋之后却变成了结构的重要类型,如颜真卿、赵孟頫和何绍基的楷书,它们已经超越了自然书写的技术要求,而上升为一种艺术创造了。
汉末至清代之前,篆隶书在社会应用和艺术领域也都持续存在着,偶尔还曾掀起过小高峰,例如唐朝时期的篆隶书。但总体而言,大多数时期是处于低谷的。其中特别值得在此加以讨论的现象有二:第一个现象是宋元时期篆书书写中的“烧毫”问题。烧毫意味着破坏毛笔笔锥的自然形态,以适应其时篆书笔画前后皆圆的典型造型,笔尖在起笔、收笔时如果没有特殊书写技巧(如“藏锋”“回锋”等)是不易获得这种造型的。第二个现象是宋元明时期隶书中普遍存在的“隶楷”笔形。这种笔形的特点是:大量笔画的起笔部分与楷书十分相似,转折也经常呈现为方折形态,仅在波磔上保留隶书形态。经典汉碑拓本在宋元明时期是有所流传的,当时部分书家对隶书的学习也不可谓不用功,但最终没有产生大家,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受到毛笔笔锥自然书写时容易产生的“斜切角”等特点的制约,没有找到用毛笔“拟写”典型汉碑的形意的方法。
宋、元、明时期篆隶书的这两个问题,直到清代才得以解决。篆书的解决之道首先是放弃对前后皆圆笔形的拘泥,允许甚至鼓励笔毫出入时产生形态变化。众所周知,这一变化开始于邓石如,吴玉如说“篆书到邓石如才是写出来的”,指此而言。其后的赵之谦、徐三庚等,将笔锋出入的变化多端提升为重要的艺术手段。隶书的解决之道是对斜切角这一“类楷”起笔形态的全面回避。郑簠、王时敏、邓石如等隶书家都是如此。据笔者观察,这主要得益于对“蚕头”法也就是逆锋起笔的推广运用。无“蚕头”法可直接推广的竖画,其起笔(包括横折)的“类楷”形态则比横画要多,即使到了隶书复兴已经达到高峰的伊秉绶的笔下,仍是如此。
清以后,宣纸和长锋羊毫普及,北碑被激活,在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下,金石拓本中因剥泐而造成的笔画轮廓残缺起伏等效果,在水墨洇染中得以在宣纸上复现,导致“金石气”成为时代的审美趣尚,并由此进一步激发了笔法探索的热情。虽然依旧是“右手执毛笔”书写,但无论是执笔法、运笔法还是笔锋的运动方式,都出现了大量新理异态,许多时候,笔锋在出入之际根本是散乱扭绞的,已经难以从“锥体”的角度加以分析,更不必说传统的“藏锋”“露锋”“中锋”“侧锋”“偏锋”等。“笔墨”自生“情韵”,其手法,就不再是“右手执毛笔”自然书写所能限制的了。许多创造性的风格,恰恰不是“右手执毛笔”自然书写所能达到的,比如何绍基“回腕法”所造成的拗峭扭曲的笔形、费新我因右手病废而用左手写成的跌宕摇曳的字形。在“艺术化”的目标下,手的生理潜能和毛笔的物理潜能得到越来越丰富的开发,中国书法的形式,也因此而变得越来越丰富,可供人心寄寓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宽博。
在这个背景下,即便是早期自然书写的字迹如侯马盟书等,经过艺术家之手重新进入到书法场域中,也不能仅凭其自然书写的原貌,而要经过大量创造性的“笔墨”转换以提升“情韵”。当代书法以早期简牍为师法的作品中,除了部分小字之外,绝大多数都融入了源于金石拓本而生成的笔法和墨法,“刻”“铸”“书写”在新的艺术理念下,打成了一片,共同营造了书法传统资源全方位激活的局面。
认识到这一点,传统历史资源,才有可能在新时代获得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更好地形成创造性转化。就此而言,我们对于侯马盟书(以及其他早期手写字迹)的运用,无疑还有很大的空间。无论在文字层面上和书法层面上,都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继续研究。

编号3:6 长17.9cm 板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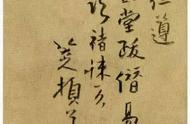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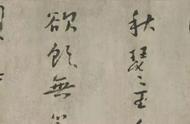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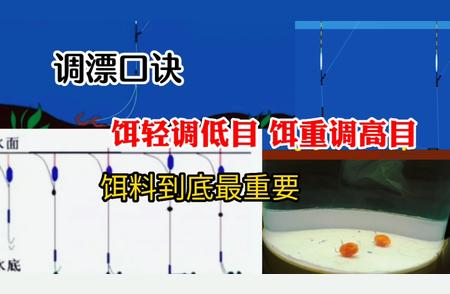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1852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1852号